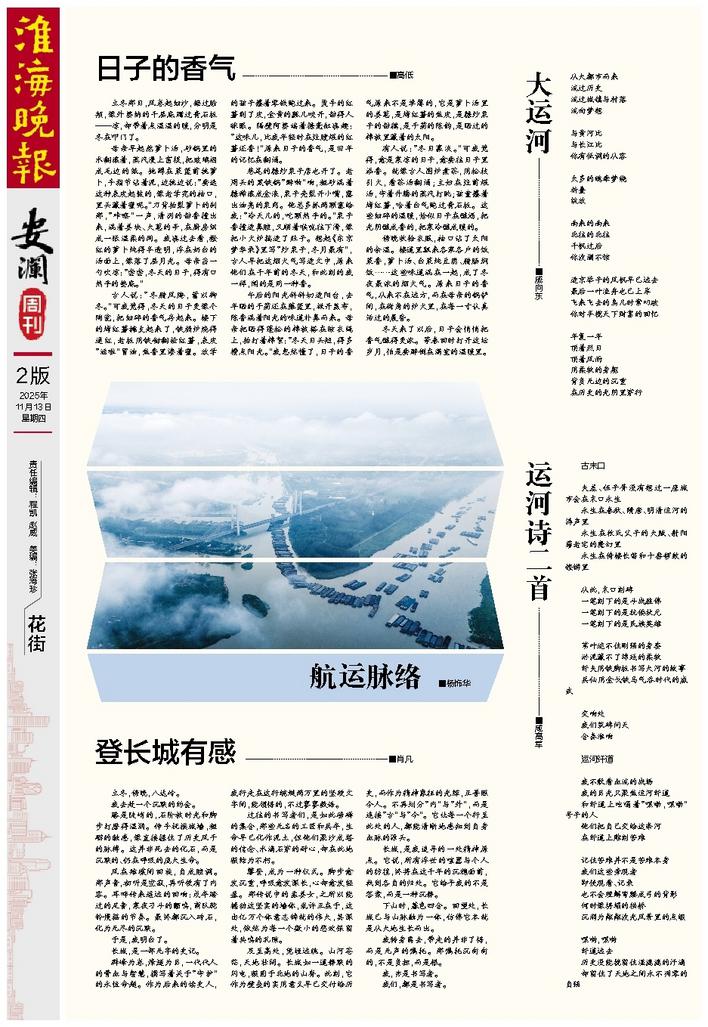立冬那日,风卷起细沙,擦过脸颊,像外婆纳的千层底蹭过青石板——凉,却带着点温温的暖,分明是冬在叩门了。
母亲早起熬萝卜汤,砂锅里的水翻滚着,蒸汽漫上窗棂,把玻璃洇成毛边的纸。她蹲在菜篮前挑萝卜,手指节沾着泥,边挑边说:“要选这种表皮起皱的,像老学究的袖口,里头藏着蜜呢。”刀背拍裂萝卜的刹那,“咔嚓”一声,清冽的甜香撞出来,混着姜块、大葱的辛,在厨房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我凑过去看,橙红的萝卜炖得半透明,浮在奶白的汤面上,像落了层月光。母亲舀一勺吹凉:“尝尝,冬天的日子,得有口热乎的垫底。”
古人说:“冬腊风腌,蓄以御冬。”可我觉得,冬天的日子更像个陶瓮,把细碎的香气存起来。楼下的烤红薯摊支起来了,铁桶炉烧得通红,老板用铁钳翻捡红薯,表皮“滋啦”冒油,焦香里渗着蜜。放学的孩子攥着零钱跑过来。烫手的红薯剥了皮,金黄的瓤儿咬开,甜得人眯眼。隔壁阿婆端着搪瓷缸凑趣:“这味儿,比我年轻时在灶膛煨的红薯还香!”原来日子的香气,是旧年的记忆在翻涌。
巷尾的糖炒栗子店也开了。老周头的黑铁锅“噼啪”响,粗砂混着糖稀滚成金浪,栗子壳裂开小嘴,露出油亮的栗肉。他总多抓两颗塞给我:“冷天儿的,吃颗热乎的。”栗子香撞进鼻腔,又顺着喉咙往下滑,像把小火炉揣进了肚子。想起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写“炒栗子,冬月最有”,古人早把这烟火气写进文中,原来他们在千年前的冬天,和此刻的我一样,闻的是同一种香。
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阳台,去年晒的干菊还在藤篮里,掀开盖布,陈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扑鼻而来。母亲把晒得蓬松的棉被搭在晾衣绳上,拍打着棉絮:“冬天日头短,得多攒点阳光。”我忽然懂了,日子的香气原来不是单薄的,它是萝卜汤里的姜葱,是烤红薯的焦皮,是糖炒栗子的甜糯,是干菊的陈韵,是晒过的棉被里藏着的太阳。
有人说:“冬日寡淡。”可我觉得,愈是寒凉的日子,愈要往日子里添香。就像古人围炉煮茶,用松枝引火,看茶汤翻涌;主妇在灶前煨汤,守着升腾的蒸汽打盹;孩童攥着烤红薯,哈着白气跑过青石板。这些细碎的温暖,恰似日子在酿酒,把光阴酿成香的,把寒冷酿成暖的。
傍晚收拾衣服,袖口沾了太阳的余温。楼道里飘来各家各户的饭菜香,萝卜汤、白菜炖豆腐、腊肠焖饭……这些味道混在一起,成了冬夜最浓的烟火气。原来日子的香气,从来不在远方,而在母亲的锅铲间,在街角的炉火里,在每一寸认真活过的晨昏。
冬天来了以后,日子会悄悄把香气酿得更浓。等春回时打开这坛岁月,怕是要醉倒在满室的温暖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