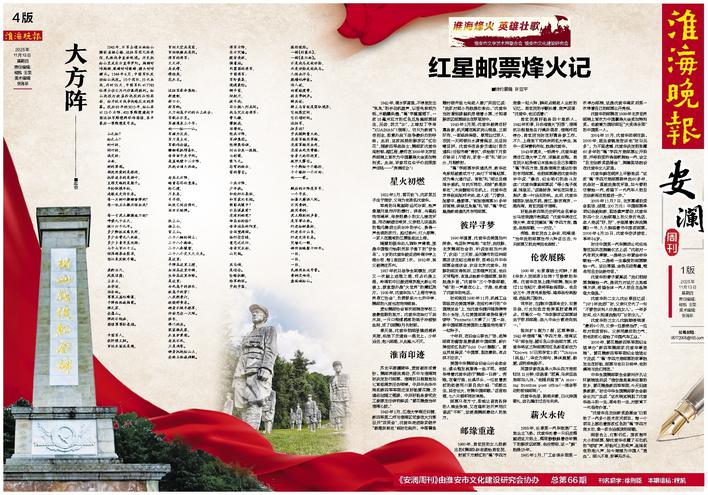■特约撰稿 许亚平
1942年,滴水茅屋里,不停地发出“轧轧”的手动机器声,以废电报纸为纸,木戳蘸朱墨,“稿”字重重落下,一枚18毫米见方的红色五角星邮票诞生,无齿,阴文“20”,上端拉丁字母“XUAINAN”(淮南)。它只为新闻飞传而生,却意外刻下战争最炽烈的呼吸。此后,这枚孤绝的解放区“红印花”,随新四军老战士、集邮家沈曾华闯封锁、越江海,最终在1999年北京世界邮展上首次为中国赢得大金奖加特别奖。此刻,评委耳边似乎仍回荡那声低吼——“突围成功”!
星火初燃
1922年2月,雪花纷飞,沈家第五子生于淮安,父母为他取名沈曾华。
军阀的马靴踏碎运河冰面,枪声像腊月里炸开的爆竹。深夜,乌篷船悄悄离岸,母亲把最小的女儿搂在怀里,用衣襟堵住啼哭,父亲把几块温热的银元塞进士兵冰冷的手心,换得一声含混的放行。船过扬州,灯火渐稀,一家人在腥咸的江雾里抵达上海。
隔壁的振华幼儿园铃声清脆,那是中国银行给职员孩子备下的“安全岛”。9岁的沈曾华被送进岭南中学上海分校,每2周回家1次。1932年,其父被调往苏州。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沈家又一次踏上逃难之路,终点仍是上海。岭南初中已搬进南京路大新公司楼上,教室窗外是“大世界”的霓虹残片。1939年,沈曾华加入“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”,负责联系六七所中学,集邮的火苗也在悄悄燃烧。
麦伦集邮协会首次邮展在学校二楼最显眼的地方。沈曾华在油灯下刻木刻,一只口衔橄榄枝的鸽子冲破铁丝网,成了《邮集》月刊封面。
春天里,沈曾华把邮册缝进棉袄夹层,沿地下交通线一路北上。少年远去,炮火邮路,从此星火不灭。
淮南印迹
苏北平原霜降早,麦苗被冻成青针。集邮界暗流涌动,苏中与淮南同时决定发行邮票。淮南抗日根据地如匕首抵南京汪伪咽喉。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迁至盱眙黄花塘,交通总站随之落脚。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工委原主任侯明铎说:“黄花塘是当年淮南心脏。”
1943年1月,江淮大学南迁旧铺,新四军第二师与淮南区党委在大刘郢召开“双英会”,沈曾华走进陈家砖井“新路东报社”临时印刷所。半塔镇鱼塘村砖井组七旬老人姜广兵回忆说:“我家对面小沟就是印报处。”沈曾华当时看到脚踏机旁堆着小票,才知道解放区邮票诞生在茅草房中。
1943年2月底,沈曾华被调往盱嘉县委,机关藏在高家岗山窝里,三面环沟,一面临洪泽湖。春荒凶过敌人,农民一天两顿白水煮青豌豆,无豆则嚼豆饼。沈曾华在县委交通站(即交通科)任秘书兼“青抗”,供给制下月资仅够买1斤猪肉,家信一枚“私”邮20分,月限数封。
“稿”字邮票专供通讯员,新华社电报纸被裁成方寸,油灯下写稿贴票,成为烽火通行证。首批“私”邮出自桐城手摇机,与抗币同印,后转“新路东报社”,木刻翻到石印机上。沈曾华在京寻到刻版师米纳,老人说:“刀要快,版要平,墨要厚。”首版淮南票30多年后首展,淡绿五角星“私”邮,“稿”字红星是新闻通讯员专用邮票。
彼岸寻梦
1990年盛夏,沈曾华去美国加州探亲。电话铃声响起:“您好,我姓解,北京集邮协会的,听说您到加州来了,欢迎!”三天前,圣何塞市的亚洲邮票店店主贴出海报称,即将召开中华邮票会座谈会,欢迎北京沈曾华。姓解的邮友得知后,立即循声而至,他白天写程序,夜里点检新中国邮票,缺的就是乡音。“沈曾华”三个字像邮戳,“啪”的一声盖在心上。于是,他拨通了沈曾华的电话。
时间倒回1980年11月,机械工业部组团去美国考察,在纽约举行的“中国展览会”上,当沈曾华摊开随身携带的小全张,几位美国邮商俯身细看并惊呼:“Fantastic(太棒了)!”那一刻,新中国邮票在美国的土壤里悄悄埋下一粒种子。
十年后,在旧金山联合广场,老牌邮商的橱窗里摆满新中国邮票,标价牌变成红色的“Sold Out(售罄)”。营业员耸肩说:“中国票,现在最热,有点供不应求。”
美国中华集邮会旧金山分会老会长,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。他驱车带着沈曾华进行“集邮一日游”。傍晚,在餐厅里,长桌尽头,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用川音自我介绍:“成都出生,延安长大,专集中国邮戳。”话音刚落,七八只酒杯同时举起。
邮票只有方寸,却能让语言各异的人围坐争辩,又在碰杯时齐声用汉语说“干杯”,这便是集邮最动人的地方。
邮缘重逢
1980年,周世民的女儿把新出的《集邮》杂志递给周世民,封面下方鲜红的“稿”字四方连像一粒火种,瞬间点燃老人尘封的记忆。周世民的手颤抖着,连声说道:“沈曾华,他还活着!”
周世民是盱眙县四十里桥人。1942年初春,日伪准备大“扫荡”,淮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,淮南师范停办,周世民当时在盱嘉县委工作。不久,上海地下党派来两名大学生,其中一名背着帆布包,就是沈曾华。
1943年夏末,一纸调令,沈曾华被调往江淮大学工作,须星夜启程。周世民从贴身笔记本里抽出自己珍藏的“稿”字四方连,那是淮南交通站印制的专用邮票。他把邮票塞进沈曾华的手中说:“拿去,纪念咱们的战斗友谊!”沈曾华攥紧邮票说:“等小鬼子滚蛋,城里见。”说罢转身,背包在田埂上起伏,像一叶远去的帆。此后,沈曾华随部队转战苏皖、渡江、解放南京,一路向南。周世民留守淮南。
盱眙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马培荣摊开档案说:“沈曾华调往江淮大学,周世民赠其‘稿’字四方连,墨迹、战地邮戳,一一对应。”
傍晚,周世民合上杂志,呢喃道:“当年我把邮票当作火种送出去,今天邮票又把我带回他跟前。”
伦敦展陈
1990年,伦敦泰晤士河畔,7框《华东人民邮政》如同7节静默的车厢。沈曾华在地上摊开邮集,指尖掠过112张贴片,像将军检阅部队。他自设三令:序言电报般短、编排战役图般准、选品刺刀般利。
写序时,左摊《中国革命史》,右摆目录,灯光如迫击炮弹直射凌晨两点。终稿仅一句:“华东解放区邮票诞生于敌后邮路,战火中由分散走向统一。”
规则扩5框为7框,区票稀缺。1942年淮南“稿”字四方连、淮南区“平”邮全张、赭石色山东战邮方票,沈曾华将这三种邮票用红色标签标注为“Known 3(已知存世3枚)”“Unique(孤品)”,译史为邮句,黑体眉题、副题、说明排枪般齐。
英国评委在盐阜火车头四方连前驻足12分钟,低语道:“若真,马来亚战地邮如儿戏。”他随后留言“A moving frontline post office(一座会移动的前线邮局)”。
沈曾华合册,硝烟未散,已化异国敬礼,齿孔缝住过去与未来。
薪火永传
1953年,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尘土飞扬。沈曾华拎着一只旧皮箱踏进这片热土,箱底静静躺着往年集下的解放区邮票,他没想到,这一“躺”就是25年。
1961年2月,厂工会俱乐部第一次举办邮展,这是沈曾华离家后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邮票公开亮相。
沈曾华的邮集在1999年北京世界邮展上首次为中国赢得大金奖加特别奖。他被誉为国际邮坛“大奖俱乐部”的中国第一人。
2004年10月,沈曾华因病住院。2005年,医生委婉地告诉他“时日无多”。为不留遗憾,沈曾华决定把珍藏60多年的“稿”字四方连邮票公开拍卖,并将拍卖所得悉数捐给一汽,设立“自主创新奖励基金”,捐赠现场就设在沈曾华女儿家里。
沈曾华躺在病床上平静地说:“这枚‘稿’字四方连邮票陪伴我60多年,抗战时一直被我揣在怀里,如今要把它献给一汽,希望下一代汽车人把自主创新再往前推进一步。”
2005年11月7日,北京嘉德拍卖会现场,槌落,200万元!中国邮票单项纪录被刷新,现场掌声雷动,沈曾华的四个女儿给病榻上的父亲打电话,老人连说“好,好”,手里捧着《洪流集藏》一书,久久凝视着书中那枚邮票。2006年4月23日,沈曾华安详辞世,享年84岁。
时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在捐赠仪式上说:“沈老对一汽有两大奉献,一是将25年黄金年华献给一汽,二是将一生挚爱的邮票献给一汽。这份厚望,金钱无法衡量,唯有用自主创新作答。”
沈曾华的妻子黄真说:“我们把邮票捐赠给一汽,是因为对这片土地感情太深,希望全体一汽人把自主品牌做大做强。”
沈曾华的二女儿沈长春回忆说:“1971年我进厂时,父亲只交代了一句‘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女儿’。一年多时间,没人知道我是沈厂长的女儿。”
沈曾华的三女儿沈晓珊哽咽道:“最后9个月,父亲一边接受治疗,一边校对拍卖资料。父亲用最后的力气,把他的初心留给了中国汽车工业。”
2008年,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举办“新四军集邮家沈曾华事迹展”。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馆长卞龙说:“‘稿’字四方连邮票的故事就发生在盱眙,邮票与他日日相伴,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。”
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顾问许孔让环顾展馆后说:“淮安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,黄花塘是新四军军部,今天旧貌换新颜。”时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刘广实说:“这次展览展现了沈曾华战斗的一生、革命的一生,对教育下一代很有价值。”
“沈曾华自主创新奖励基金”已资助了一汽多个技术攻关项目。每一个项目上都印着那枚红色的“稿”字四方连水印,像一枚永远滚烫的邮戳。
邮册合上,灯影仍红。那枚指甲大小的邮票,替沈曾华收藏了石印机的“嗒嗒”声、盱眙河上的桨声、盐城夜空的炮火声,如今继续为中国人“造血”。邮火不息,故事无尽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