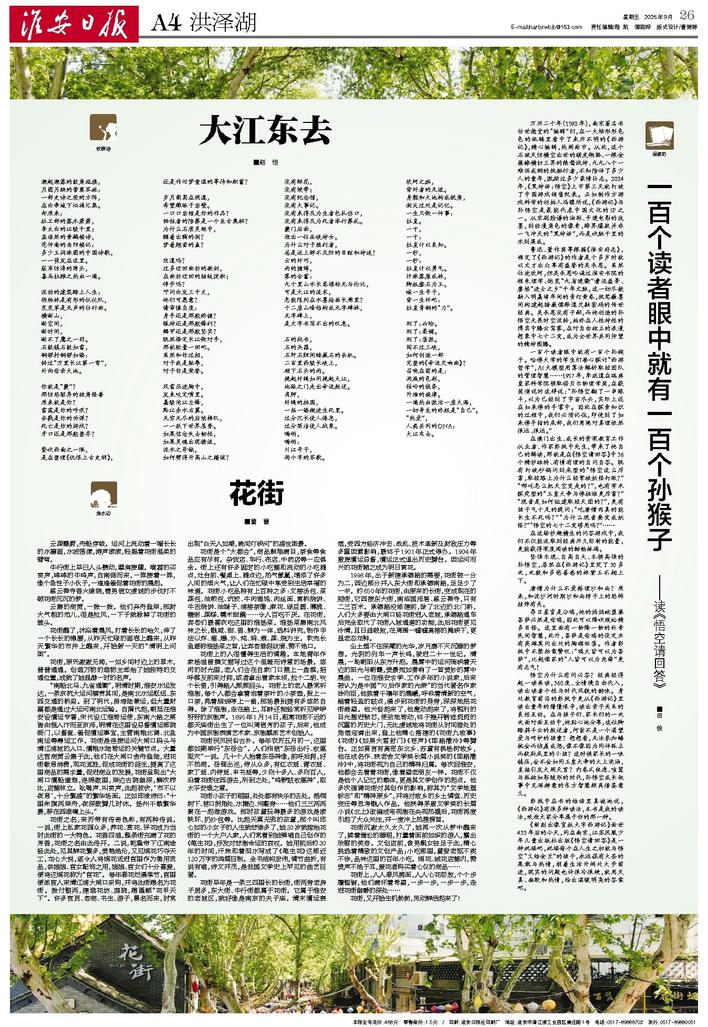■董 蕾
云蒸霞蔚,舟船穿梭。运河上流动着一幅长长的水墨画,水波荡漾,涛声滚滚,轻摇着花街温柔的臂弯。
牛行街上早已人头攒动,摩肩接踵。喧嚣的买卖声,哞哞的牛鸣声,自南侧而来,一阵接着一阵,像个急性子小伙子,一遍遍催促着花街的晨起。
慈云禅寺香火缭绕,善男信女虔诚的步伐打不破花街沉沉的梦。
云集的商贾,一拨一拨。他们弃舟登岸,那财大气粗的范儿,很是拉风,一下子就掀掉了花街的盖头。
花街醒了,沐浴着晨风,打着长长的哈欠,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,从昨天忙碌的画卷上醒来,从昨天繁华的市井上醒来,开始新一天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花街,原先寂寂无闻,一如乡间村边上的草木,普普通通。创造万物的造物主却给了她独特的交通位置,成就了她显赫一时的名声。
“南船北马、九省通衢”,明清时期,淮安水运发达,一条京杭大运河横贯其间,是南北水运枢纽、东西交通的桥梁。到了明代,虽海陆兼运,但大量财富都是通过大运河南北运输。自隋代起,朝廷在淮安设漕运专署,宋代设江淮转运使,东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师,明清在这里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,以督查、催促漕运事宜,主管南粮北调、北盐南运等筹运工作。花街是连接运河大闸口码头与清江浦城的入口、漕粮水陆转运的关键节点。大量达官商贾云集于此,他们在大闸口舍舟登陆,进花街歇息消费,观花览胜,促成花街的诞生,提高了这里商品的需求量,促进商业的发展,花街呈现出“大闸口漕船逶迤,连绵数里,岸边古院幽深,鳞次栉比,店铺林立。吆喝声、叫卖声,此起彼伏,‘市不以夜息’,十分繁盛”的繁华场面。正如邱浚诗曰:“十里朱旗两岸舟,夜深歌舞几时休。扬州千载繁华景,移在西湖嘴上头。”
花街之名,来历带有传奇色彩,有两种传说。一说,街上私家花园众多,养花、赏花、评花成为当时此街的一大特色。花香四溢,整条街充满了花的芳香,花街之名由此传开。二说,乾隆帝下江南途经此处,见其鲜花繁多,美艳绝伦,又见绢花巧夺天工,龙心大悦,遂令人将绢花送进宫里作为御用贡品,供娘娘、宫女配饰之用,娘娘、宫女们十分喜爱,便将这绢花称为“宫花”。每年春花烂漫季节,宫里便派宫人来清江浦大闸口采购,并将此街赐名为花街。拨付银两,建造花坊、庭院,赐匾额“花甲天下”。许多官员、客商、书生、游子,慕名而来,时常出现“白天人如潮,晚间灯映河”的盛世图景。
花街是个“大都会”,商品琳琅满目,茶食等食品应有尽有。杂货店、车行、布店、中药店等一应俱全。街上还有许多固定的小吃铺和流动的小吃摊点,灶台前、餐桌上、摊点边,热气氤氲,增添了许多人间的烟火气,让人们在忙碌中享受到生活幸福的味道。花街小吃品种有上百种之多:文楼汤包、菜蒸包、油煎包、炕饺、牛肉馄饨、肉丝面、黄桥烧饼、牛舌烧饼、油端子、浦楼茶馓、麻花、绿豆圆、薄脆、糖粥、蒸糕、糯米甜藕……令人百吃不厌。在花街,宾客们最喜欢吃这里的淮扬菜。淮扬菜集南北风味之长,融咸、甜、香、鲜为一体,选料讲究,制作手法以炸、熘、爆、炒、炖、焖、煨、蒸、烧为主。软兜长鱼堪称淮扬菜之首,让宾客垂涎欲滴、赞不绝口。
花街上的人很懂得生活的情趣。本地青年作家杨溢曾撰文描写过这个温暖而诗意的场景。悠闲的时光里,老人们会在自家门口摆上一盘棋,招呼棋友前来对弈,或者拿出看家本领,拉个二胡、吹个长笛,引得路人频频回头。花街上的老人最常听淮剧,每个人都会拿着泡着茶叶的小茶壶,抿上一口茶,晃着脑袋哼上一番,那场景别提有多悠然自得。除了淮剧,走在路上,耳畔还能经常听见咿咿呀呀的京剧声。1895年1月14日,距离花街不远的都天庙街出生了一位叫周信芳的孩子,后来,他成为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、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。
花街民风民俗古朴。每年农历五月初一,这里都如期举行“东岳会”。人们相信“东岳出行、收瘟驱灾”一说。几十个人抬着东岳神像,前呼后拥,好不热闹。岳驾出巡,侍从众多,有红衣班、青衣班、家丁班、内侍班、申书班等,少则十多人、多则百人,沿着花街往西游去,所到之处,“鸣锣鼓收瘟神”,取太平安逸之意。
花街小孩子的眼里,处处都有快乐的去处。梧桐树下、巷口拐角处、水塘边、沟壑旁……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做游戏。那时孩童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滚铁环、扔沙包等。比起天真无邪的孩童,那个叫邱心如的小女子的人生就悲惨多了,她20岁就嫁给花街的一个大户人家,人们常看到她弹唱自己创作的《笔生花》,抒发对悲剧命运的哀叹。她用前后约30年的时间,汗珠和着泪水写成了《笔生花》这部近120万字的鸿篇巨制。全书结构宏伟,情节曲折,有说有唱,诗文并茂,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曲艺巨著。
花街早年是一条三四里长的长街,街两旁老房子居多,东大街、牛行街都属于花街。它属于淮安的老城区,就好像是南京的夫子庙。清末漕运衰落,受西方经济冲击、战乱、技术革新及财政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,最终于1901年正式停办。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,漕运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因运河而兴的花街随之成为明日黄花。
1998年,出于新建承德路的需要,花街被一分为二,西边部分并入东大街和承德南路,足足少了一半。约650年的花街,由原来的长街,变成现在的短街,它西接东大街,南临国师塔、慈云禅寺,只有二三百米。承德路没修建前,除了北边的北门桥,人们大多要由大闸口经花街进入老城,承德路通车后完全取代了花街入城通道的功能,此后花街更见冷清,且日益破败,在周围一幢幢高楼的掩映下,更显老态龙钟。
尘土埋不住深藏的光华,岁月磨不灭沉睡的梦想。光阴的列车一声长鸣,驶进二十一世纪。清晨,一轮朝阳从东方升起。晨雾中的运河倒映着天边的阳光与朝霞,美景宛如奏响了一首美妙的雾中晨曲。一位在淮安求学、工作多年的小说家,后来被认为是中国“70后作家的光荣”的当代著名作家徐则臣,他披着千禧年的晨曦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踏着轻盈的鼓点,漫步到花街的身旁,深深地把花街凝望。他兴奋起来了,他激动起来了,将锐利的目光插进锁芯,使劲地转动,终于推开锈迹斑斑的沉重的历史大门,无比虔诚地将花街从时间暗处的角落迎请出来,登上他精心搭建的《花街九故事》《花街》《如果大雪封门》《苍声》《耶路撒冷》等舞台。正如莫言有高密东北乡、苏童有枫杨树故乡,他在成名作、获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《耶路撒冷》中,将花街视为自己的精神归属。每次回淮安,他都会去看看花街,像看望老朋友一样。花街不仅是他个人记忆的载体,更是其文学创作的起点。他多次强调花街对其创作的影响,称其为“文学地理标志”和“精神原乡”,并将对故乡的乡土情谊、历史变迁等思考融入作品。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北上》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,花街再度引起了大众关注,并一度冲上热搜榜首。
花街沉寂太久太久了,她再一次从梦中醒来了,揉着惺忪的睡眼,打量着面前如织的游人,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文创店前,俊男靓女驻足于此,精心挑选着精致的文创产品;小吃部里,童叟老妪不疾不徐,品味这里的百年小吃。绢花、绒花店铺内,赞美声不绝于耳,爱花者购买着心仪的商品……
花街上,人人春风拂面,人人心花怒放,个个步履铿锵,他们满怀着希望,一步一步,一步一步,走进花街幽静的深处……
花街,又开始生机勃勃,灵动鲜活起来了!